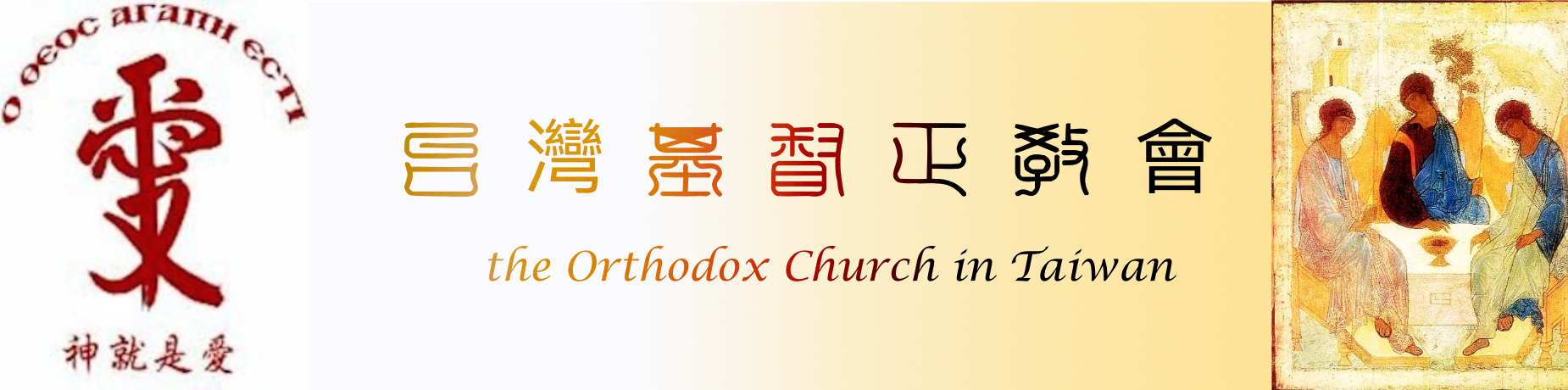婚姻 – 正教會的婚姻觀
MARRIAGE – An Orthodox Perspective
John Meyendorff著
V. 獨立於聖餐禮儀之外的婚禮
直到公元九世紀,教會仍然沒有任何結婚儀式,可以從神聖的聖餐禮儀當中獨立出來[註七]。一般而言,在公證婚姻後,基督徒夫妻一起參加聖餐禮儀 —- 依據Tertullian的說法 —- 這個聖餐內的結合,正是婚姻的印記,包含了先前所討論的一切基督教式的責任。
然而,自從第四世紀以來,東方的基督教作家,提到了一個聖事中的特殊典禮:在聖餐禮儀中所舉行的「加冕」儀式。根據聖.金口若望的解釋,這個加冕象徵了戰勝「情慾」,因為基督徒的婚姻 —- 是一個永恆的聖事 —- 不會「跟隨著肉體」而消逝。從聖.狄奧多若(St. Theodore Studite,卒於公元826年)的書信中,我們了解到,在週日的聖禮儀當中,加冕儀式總會伴隨著一段由主教或神父「在眾人面前」唸誦的簡短禱文。這段禱文,來自聖.狄奧多若,禱詞如下:「哦!主。祢自己,從神聖的住處降下了恩惠,並與祢的僕人與侍女緊緊相連。還賜予他們祢最和諧無二的心;使他們成為圓滿的一體;使他們的婚姻榮耀,使他們的床純潔無污,讓他們的生活,毫無缺點。」(Letters I, 22, PG 99, col. 973)同一時期的聖禮儀相關書籍(例如著名的codex Barberini)其中,有一些簡短的禱文,與聖.狄奧多若所引用的相類似。在聖禮儀當中,這些祈禱文都可以拿來誦讀[註八]。
儘管如此,這個簡化的加冕儀式的出現,並非意味著,它立刻成為所有基督教徒訂立婚約時之必要禮儀。一些著名的法律典籍,例如詳細記載了教會和政府之間關係的Epanagoge(中譯註:Epanagoge為拜占庭皇帝巴西爾一世時代編纂的法典) —- 其作者,極有可能是大主教Photius(857-867, 877-886)—- 它也為基督徒提供了締結婚姻的三種方式:Photius這樣描述:「婚姻,是丈夫與妻子之間的聯姻,是整個生命的結合;它藉由領受祝福、加冕儀式或訂立契約而完成。」(XVI,1)從第六世紀至第九世紀,宗主國的法律都趨向於賦予教會在婚姻上愈來愈多的控制力(請參見novella 64 of Justinian等例子),但是,政府從不把「加冕儀式」變成一個法律上的義務。
關於此,決定性的一步,在於第十世紀初。就在加冕儀式從聖餐禮儀中獨立出來的同時,這個措施也相應產生。究竟是什麼因素促成了這個徹底的變革?如果不是因為婚姻的意義本身,至少是為了大多數信徒對婚姻的理解吧。
關於這個問題,從王權法令強制執行此項變革的事例當中,就可以輕易的找到答案。拜占庭皇帝利奧六世(Leo VI,卒於公元912年)頭一次惋惜的表示,在先前王朝的律法當中,領養小孩與婚姻這兩項法律行為,一直被單純的認定為民事上的手續。他接著宣告,這兩項行為 —- 只要當事人是自由公民,而非奴隸 —- 行使之後,都會受到教會儀式的認可。沒有接受教會祝福的婚姻「將不被承認」,而且是一種非法的同居行為。[註九]
這段文字中的許多看法,都值得我們關注 —- 例如,婚姻與收養小孩之間的比較[註十],現實上,奴隸並未受這個新法令的保護。然而這個法令,最重要的意義是,教會獲得了賦予婚姻合法性的職責。第九世紀的基督教國家裡,儘管教會和政府之間的關係十分密切,但是,這樣的職責,確是相當罕見,也令人震驚。在利奧六世之前,一個公民可以走進一個教會所不允許的婚姻(如再婚、三度結婚、異教徒通婚...等),而且這樣的行為完全合法。假如當事人是一位基督徒,他的行為會招致一段悔罪期,並且被逐出教會(就如同下文中所描述的),然而,他在法律之前,仍擁有良好的立足點。在利奧六世之後,教會就必須裁決所有婚姻的合法性,甚至是那些違反基督教準則的部分。當然,這個新的情況,原則上,在維持公民的道德行為上,給予教會一個有利位置。但是,在實際上,公民畢竟不都是聖人,教會的服務,不僅只於祝福婚姻,甚至還要終結婚姻(也就是,授允「離婚」)。因此,「世俗」與「神聖」的分別,墮落的人類社會與上帝國度之間的差異,契約式的婚姻與婚姻聖事的分別,都被不公平地湮沒了。
教會必須為這個新的社會責任,付出高度的代價,也必須承擔一切;關於婚姻,教會必須將其理想化的態度「世俗化」,確實的拋棄那些悔罪性的責罰。但是,這種做法可能實現嗎?例如,在一兩年間,禁止一個再婚的寡婦領受教會的祝福,然而,這種行為卻隱含著對民法權利的剝奪。只要 —- 在教會中領受婚姻聖事 —- 成為法律上的必要條件,就無可避免要對各式情況妥協;同時,「婚姻是一個獨一無二且永恆的結合」這個反映出基督與教會的合一的概念 —- 也會因為良知上的虔敬心,使得它在教會內最理想的實踐當中,遭受徹底廢除的命運。利奧六世皇帝本身,即novella的作者(中譯註:利奧六世皇帝用希臘文寫成帝國法律,成為拜占庭帝國的法典。),強迫教會認可他與Zoe Carbonopsina於公元906年的第四度婚姻。
教會唯一無法接受的妥協,就是減去聖餐禮儀的神聖性:教會絕對不能,將聖餐給予一個非東正教徒,或是一對再婚的配偶。因此,必須要建立一個獨立於聖餐禮儀之外的儀式。只要「教會內的婚姻」,成為一種法律上的需要,「教會內的婚姻」與聖餐禮儀之間的清楚連結,就不復存在,這樣的事實,使得這種變革,更能被大家所接受。
然而,即使是利奧六世所著的帝國法典novella,也無法完全禁止教會成員當中,某些特殊族群,透過一個包含聖餐禮儀的婚姻聖事,而不是獨立於聖餐禮儀之外的(往往也是奢華的)「加冕」儀式 —- 來完成婚禮。奴隸階層的人們 —- 也就是說,超過帝國總人口數一半的人,不適用此新法律。之後,Alexis I Comnenos (1081-1118)皇帝解決了奴隸階層的婚姻法與自由公民的婚姻法之間的矛盾,他頒布了另一個novella,使得「加冕」儀式,對於奴隸階層的人來說,也成為一項法律義務。
在創建獨立於聖餐禮儀之外的「加冕」儀式的同時,教會並沒有忘記,婚姻與聖餐禮儀之間,那個最初的、最直觀的連結。此連結,清楚展現在聖.西默盎(St. Symeon of Thessalonica)的著述(書末索引用的附錄IV)當中。古老形式的禮儀,包含了結婚新人雙方的共融,然而,其中聖事(聖餐禮儀)的部分,卻予以保留 —- 禮儀書上說:「如果他們堪當」。領受聖餐之前,神父大聲念誦出:「為了聖潔而準備奉獻的神聖獻禮。」並且伴隨著聖餐禮儀的聖詩:「我將領受主的聖杯。」[註十一]十五世紀末,教會的婚禮包含了共融的部分,而聖事(聖餐禮儀)的部分,卻予以保留:這樣的做法,曾出現於十三世紀的希臘禮儀書手稿,十五世紀時,才出現在斯拉夫禮儀書當中 [註十二]。在結婚的新人雙方「不堪當」的情況中 —- 也就是說,當婚姻不符合教會的法規時 —- 他們所參與的,並不是一個聖事,而只是共進一杯盛了神父祝福過的酒的共融之杯。這樣的做法 —- 就像是在聖禮儀結束前,把受過祝福的麵包或聖餅(antidoron),分配給那些「不堪當」領受聖餐的人 —- 這樣的做法,已傳至全世界,至今仍被採用。然而,即使是當代的禮儀,也保留了許多特質,可以為它與領受聖餐之間最初的連結做見證。正如聖禮儀那般,一開始即大聲念誦出:「讚頌聖父、聖子及聖靈的國度」,在主禱文的唱誦之後,接著共進共融之杯(common cup),正如在聖餐禮儀當中的共融那般。
在合乎教會聖典的傳統中,和實際的傳統上,教會仍然記得,領受聖餐禮儀,才是婚姻真正的「印記」。婚姻在受洗之前就已經締結,也就是說,沒有任何「聖事」上的意義,與聖禮儀,也沒有連帶關係 [註十三]。若是一位剛受洗的基督徒,與一位女性基督徒走入第二度婚姻,只要他之前僅有過一次婚姻,就可保有接受祝聖而成為神父的資格(宗徒法典17)。另一方面,正如上文所示,若一對非基督徒夫妻,同意藉由受洗、堅振和領聖餐(共融)而加入教會,並不算是「再結一次婚」,他們共同領受的聖餐禮儀,代表著「締結於教會之外的『自然』婚姻」在基督教意義上的圓滿。
在我們的時代中,有必要(也很容易)修復婚姻與聖體聖事之間的連結。教會要以怎樣的、更好的方式,將過去所作所為中蘊含的「聖事的真正涵義」傳遞給她的子民呢?
[註七] 請參考A. Zavialov, Brak (“Marriage”), article in the Orthodox Theological Encyclopedia( in Russian), A. P. Lopukhin, ed., vol. II, Petrograd, 1903, pp. 1029-1030, 1034.中的例子。
[註八] 請見 Goar, Euchologion, repr. Graz, 1960, pp. 321-322.
[註九] A. Dain, Les Novelles de Leon VI, le Sage, Paris, 1944, pp. 294-297(Greek text and French translation), Eng. Tr. Below, p. 109.
[註十] 即使是當代,難道不值得我們用心給予「領養小孩」一個宗教上的意義嗎?
[註十一] 請參考,第十世紀在西乃山圖書館發現的一本euchologion(中譯註:正教會當中,其中一本重要的關於聖禮儀的著作);text in A.A. Dmitrievsky, Opisanie Liturgicheskikh Rukopisei, II, Εὐχολόγια, Kiev, 1901, p.31. 此為希臘各教會中所行的儀式,即使到了今日,仍會在共進共融之杯(common cup)唱誦此共融詩歌(communion hymn)。
[註十二] A. Katansky, “Towards a History of the Marriage Rite” ( in Russian ), in Kbristianskoe Chtenie, St. Petersburg, 1880, I, pp. 112, 116.
[註十三] The opposite opinion, expressed by S. V. Troitsky in his otherwise very valuable book on The Christian Philosophy of Marriage, seems to lack theological or canonical basis.